[美]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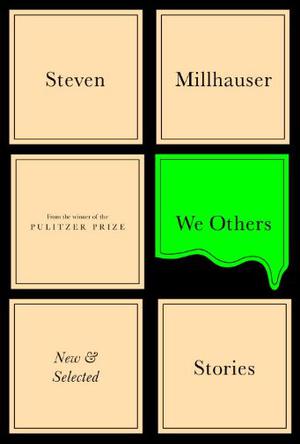
他九岁了,快满十岁,长得又瘦又高,肩胛骨就像装在纸袋里的东西一样,往外突着,蓝色泳裤是新的,这儿太紧,那儿太松,但是那一切又有什么所谓?重要的是他在这儿,站在野餐桌边,太阳照在河面上,松针和河水的气味浓烈,哪儿传来一声喊叫、一阵大笑还有收音机上放的音乐声。他的爸爸正在清理烧烤炉里的灰烬,妈妈和姐姐正在把毯子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离野餐桌不远,奶奶正在把一张铝合金折叠椅搬到一棵高大的松树那边,那棵树长在通往河边的一道陡坡边上,而他正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他真正擅长的,即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有几秒钟,大家都忘了还有他,有时候会这样,你努力不去提醒别人你在这儿。他很喜欢这个地方。野餐桌上,放着那个胖乎乎的暖水瓶,靠下边处有个喷水孔。游完泳后,他会按喷水孔上的一个按钮接一纸杯粉红色的柠檬水,发出的声音挺好听:“夫嘶,噗嘶。”他能看到野餐篮里有两盒热狗,一瓶切碎的甜泡菜,一瓶芥末酱,几个小圆面包露了出来,一盒奥利奥饼干,一袋棉花糖,侧着露出来的纸盘子,一个折着口的牛皮纸袋,也许装的是樱桃。整整一周,他都在盼望这天。这样再好不过:夏天时出去一整天,去滨河公园——熟悉的房子和空地不再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而是隔着车窗看到它们向你移来,晒暖的座位热得隔着牛仔裤也能让你感到发烫,从停车场走向河岸上方的野餐区时,你的脚底感觉到地面把你的脚底往上推。然而他现在到了这儿,就在此地,他的牛仔裤扔在后排车座上,T恤衫塞在他妈妈的草编袋子里,阳光照在野餐桌的一道边上,桌上剩余地方都是松树的荫凉,奶奶已经在支起椅子。所以这一天就要开始了,他在炎热的夜里看着路过的汽车照射的一道道光掠过他的墙壁时盼望的这一天,他到了这儿,他赶到了这儿,准备好开始了。
但是由谁来说任何事情真正开始?你可以说,在他们路过上面有“印第安湾”字样和一把印第人战斧轮廓的木制广告牌(树在一段弯路上,牌子中央从上到下有两道黄线,还有装有红色射灯的褐色木柱)时,那天就开始了。要么也许是当那辆车倒着开上行车道的斜坡,轮胎摇晃着上了齐膝深带刺灌木之间的人行道时,一切就开始了。要么,如果是在那之前,当他早上醒来,那天就像整个夏季到下午就郁闷的每天一样,在他眼前展开时开始的,那又如何?不过他只是在玩,只是闹着玩,因为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下水时开始。那是一个又一个夏天以来,他跟自己达成的共识,定好了。那天从水里开始,其他一切都导向那个时刻。
并不是说他有那么迫切想赶快开始那一切。既然他到了这儿,既然事实上等待已经结束,他喜欢把走向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刻的兴奋感再延长一点。他甚至不会游泳,抱着轮胎内胎不撒手,蹬脚。他喜欢那样,挺好的,他拿得起,放得下。不,他关心的,每次都让他感到激动的,是知道就是这样,就像他提前跟自己达成共识的那样,期待已久的河边这一天就要开始了。一切都在导向这个时刻,另外,就像一件事情导向其他事情,有种电荷,一种嗡嗡声。他全身都能感觉到。越接近,就越是有这种感觉。
在这方面,十三岁的茱莉娅跟他不一样。她铺好三张毯子不久,就会跑到陡坡边上,蹦蹦跳跳地跑下去,跑过那段窄窄的地面。她总是那样,热情投入到什么上去——钢琴课,采蓝莓,野外徒步,在海滨游乐场玩碰碰车。她觉得他小心,太矜持,甚至胆小,很可能真的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他喜欢慢慢积累,因为那样发生时,一切都让人感觉重要。这是否意味着他身上还有点没长大的样子,有一天那是要消失的,就像他突出来的肩胛骨和球形脚踝骨?
“来吧,帮下忙,队长。”茱莉娅说。他不再是无人看到了。茱莉娅不喜欢别人站在边上无所事事。他拎起毯子一角,还没明白过来,她就绕过野餐桌,朝奶奶坐着的那棵松树方向走去,她爬下陡坡看不到了。一秒钟后,又看到了她的头,接着是她全身,除了她的脚,然后她又有了脚后跟、脚趾。她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走得河水没过她的膝盖,弯下腰把水往胳膊上撩。他甚至能看到她的红色泳衣在水中的倒影破碎了。河面微有涟漪,也许是因为白桶那边有一艘快艇开过而造成的。他爸爸跟他说过豪萨托尼克河是条有潮汐的河。他记得那个词:有潮汐的。他看着的涟漪有可能是潮汐吗?豪萨托尼克。他喜欢说那个词,喜欢拉长“托”那个音,让他想到老电影里一列火车驶过一道拐弯。茱莉娅扑进水里,开始朝水桶那边游去。
“你也快点去,吉米。”他妈妈说,“这儿没事了。”他知道该开始了,你不可能把事情永远拖延下去。他走到太阳地下的几条内胎那里,拿起歪靠着另一条的那条,捏了捏上面蒙了层灰尘的橡胶,以确认不漏气。然后开始把一条内胎颠簸着滚过草地,绕过野餐桌,向奶奶坐的那棵松树滚去。
这段路不远,树荫很浓,还有点点阳光漏下。他走在软而易断的松针和海绵般的松球上,松球顶着他的脚底,似乎他走在卷起来的袜子球上。地面感觉又硬又有弹性。奶奶坐在一棵大松树旁,那棵松树略微前倾,似乎有一天它开始往前倒,却又改变了主意。左边有另外一棵松树,也往前倾,两棵树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相框,围着阳光照耀下的河面和对岸远处长着树木的小山。一切都让人有兴趣:浓荫下面那个大松果的一头在阳光下有反光,那根沾了淡红色的冰棒棍掉在一条疙疙瘩瘩的树根旁边。奶奶的椅子不是放在前廊上又长又重的那张,可以调整位置的,不,她带了那张小的,直背,很容易一拉就能打开。她穿着深蓝色的游泳衣和一双草编的拖鞋,脚趾涂成了粉红色,她浓密的头发可以说是奇怪的有点白,也有点黄的橙色。她总是哈哈笑着说她染发剂没用好。她坐在靠近陡坡边的树荫下,两腿晒太阳,书放在膝上。她的手指在关节那里曲着,她喜欢举起来给他看,看看:关节炎。那张椅子上十字交叉的条条是白色和灰绿色。他向她走去时,她扭过头,一只手按在书上,好不让它合上。
“这么说好人哪,你要下去了吗?你看茱莉娅到那边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让人们这样说话:队长,好人。是他身上的哪一点。他姐姐这时到了桶边,在仰游,蹬着脚,两只手往后划。“对,好人啊。”他说,奶奶就像他想让她做的,从喉咙深处发出沙哑的笑声,笑声中带着赞许。这一家人都说话风趣,你得时刻打起精神。如果他起床晚了,他爸爸会这样说:“昨天夜里出去喝酒回来晚了,呃,吉姆?”要么“看哪,儿子起床了。”他站在奶奶旁边,用指尖让内胎保持平衡,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奶奶手腕上的手镯,一个是玳瑁的,一个是银的,她的手指肿胀,关节处疙疙瘩瘩;经过那张椅子直到陡坡边缘的几英尺宽的地上长着一团团草,软塌塌的,看上去被晒热了;粗粗的松树根扭动着伸出斜坡,一根白色绳子吊在树根上。看到这些东西都不错,但有时你看不到。它们在导向某件事情时,你就看到了。
他往陡坡的边缘——世界的边缘——走了几步。在他身后,是坐在椅子上的奶奶,铺满松针的地面,野餐桌,其后是阳光照耀下的毯子,一片田野——但是干吗到那儿就不说了?康涅狄格州在他身后延展开来,比尔德斯利公园动物园里的猴笼,路上有石桥的麦里特主干道,然后到了西一百一十街的奶奶家,如果你再往远方,密西西比河,派克峰,加利福尼亚。这样挺好玩。你可以往两个方向都这样。他前面是斜坡,河边有沙有土的地方,茱莉娅在仰游。然后是白色的桶,对面河岸长满树木的小山,越过小山,是康涅狄格州的另一边,去科德角某种名叫神秘海港的地方看捕鲸船的那一趟,大西洋,非洲。他喜欢站在那里考虑这些事情。他在阳光下严肃地盯着河面、皱紧眉头时,喜欢在心里想象自己的形象,他用指头扶着内胎的上端,另一只手架在臀部,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的哈克贝利·芬啊,一个勇敢地背着一箭袋箭的印第安人准备下去跳上独木舟。
但是他不可能一整天都站在那儿。茱莉娅正在靠着一个桶休息,她看着他。她一只手搭着凉篷,另一只手向他挥动。来吧,队长!奶奶的眼睛从书本上抬起来看他。另外,他也想让在印第安湾的这一天开始,他真的想,即使从他到这里后,他一直努力在做的,就是尽量把它往后推。到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那棵松树的另一边硬硬的土路,大人们走那条路,要么直着走下土质松软易碎的斜坡。他用胳膊牢牢地夹着内胎迈过边缘,半是滑下去,半是跌跌撞撞地走下去,感觉到暖和而多沙的土末落在脚面,让他想起盐末洒到手里的感觉。他到了那里,他做到了,他站在一块橙色的沙土地上,小得称不上是沙滩。人们去的沙滩上有真正的沙子,有毯子、沙滩伞、海水、饮料摊、海鸥、死螃蟹、沙洲、浪。这里是河边,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是橙色的沙土地,再往下是大石头和香蒲草,别的地方水边就有树和草。这个没名字的地方感觉比沙滩更柔和,更安静,更偏僻。斜坡在他身后,颜色绿中带褐的水在他面前,白色的桶略微上下浮动,似乎河水在呼吸。
他开始滚动内胎往前走。再走九步或十步,他就到了水边。他能看到水面的细浪。如果他不知道这是一条河,他会觉得自己是站在湖边。弯向水面的树枝把两边的河弯都遮住了,你看到的,是边上有着长满树的小山的一面湖水,远处的岸边有几幢小房子,一座码头,有个身形渺小的人在那里钓鱼。他把内胎滚过沙土地,这里鹅卵石太多,但是看不到一丛丛柔韧的水草,看不到紫黑色蚌壳。一个绿色的空可乐瓶直直竖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它属于沙滩,歪在沙里,在毯子旁边,它投下了绿色的影子。模糊的脚印,一块光滑的扁平石头,适合打水漂。兴奋感在加强,他几乎走到了那里。
到水边后,他停了下来。他看好不让细浪在涌上来时碰到他的脚趾。透过河水,他能看到阳光把波纹的图案映在河底,像是光线形成的铁丝网。是这条河了,他的冒险开始于此,到了这最后一个地方,他最后一次停下脚步。
一切都导向这个时刻。不,错了,他还没到那个时刻呢,它就在他前方。这是在结束等待以及他迈进一直等待的事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吸进河水的气味,深深地吸进鼻孔。自从他今天早上醒来,自从上周那天他爸爸下班回来,手里拎着公文包还没放下就说天气不变的话,他们周六去印第安湾以来,他就一直在接近这个时刻,那就像等着去游乐场。再过一秒钟,等待就结束了,那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他一直盼望的,然而到河水边上这里,他不想让等待结束,他想竭力挽留。他站在河岸上,颜色绿中带褐的细浪消失在他的脚趾头前面。太阳在照耀着,茱莉娅在挥手示意他往前走,白色的桶轻轻地一起一伏,他想做的,是回到上面有印第安战斧的那块木制广告牌处,开始等待看到河岸。
他这是怎么回事?干吗不能像茱莉娅那样做?他很喜欢这一天,不是吗?现在他随时都会站在齐膝深的水里,用手哗哗响地撩来撩去。他会往水里走得淹到泳裤,会洒湿自己的胸口和肩膀,会跳上内胎向茱莉娅划去,会在阳光下哈哈大笑。到后来,他会扑到毯子上,感受太阳晒干他的泳裤。他会用小圆面包夹着一条热狗肠吃掉,喝暖水瓶里粉红色的柠檬水。他会因为晒太阳和感到快乐而懒洋洋的。这天结束时,他会去吱嘎作响的更衣室里换下泳裤,回家时在车上睡着,在街灯下。哪儿不对劲。他内心深处受到震动,似乎如果这天开始了,他就会失去什么东西。如果他走入水中,就会失去那种兴奋感,失去因为离他一直等待的时刻越来越近而产生的一切都重要的感觉。当你拥有那种感觉时,一切都充满了生命感,每片树叶,每块鹅卵石。可是你一开始,你就在用光一切,这一天开始从你身边溜走。他想留在一切的这一边,就守在这里。他心头一阵紧张,在阳光下,却感到一阵寒意。再过一会儿,这一天就会开始结束。一切会冲过他身边。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天几乎快结束了。他这时看到了,他看到:到处都在结束,就蕴含在开始中。他们不告诉你这件事,它藏在事情里面,在世界光亮的皮肤里面,一切都死了,没有了。太阳正在落下,这一天正在消亡。奶奶正在棺材里死去,她畸形的手交叉在胸前。他漂亮的妈妈正在变老,她的手指又粗又弯,她褐色的头发变得像白线一样。没人能阻止这样。茱莉娅正在离世,他的爸爸正在离世,那个可乐瓶正在碎裂成绿色的灰尘。一切都是乌有。如果他站着不动,如果他纹丝不动,也许他能够阻止,不让它发生。一切就会停止,没人会死。他的身体在颤抖,无法呼吸,在水边这里,他位于一切的终点。你无法活着,除非有办法拦住不让一切发生。他无法回去,因为他已经全用完了,他无法前进,因为接着就开始结束了,他被卡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一切都了无意义,就像黑暗,就像一种疾病,正在向他涌来。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只有成年人才允许看,这让他变老了,破坏了一切,他的太阳穴处感到砰砰响,他的眼睛感到砰砰响,他感到胸膛里正在形成一声尖叫,他就要倒在橙色的沙土地上。“喂,伙计!”茱莉娅喊道,他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吼叫,迈过那条线,开始了他的这一天。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