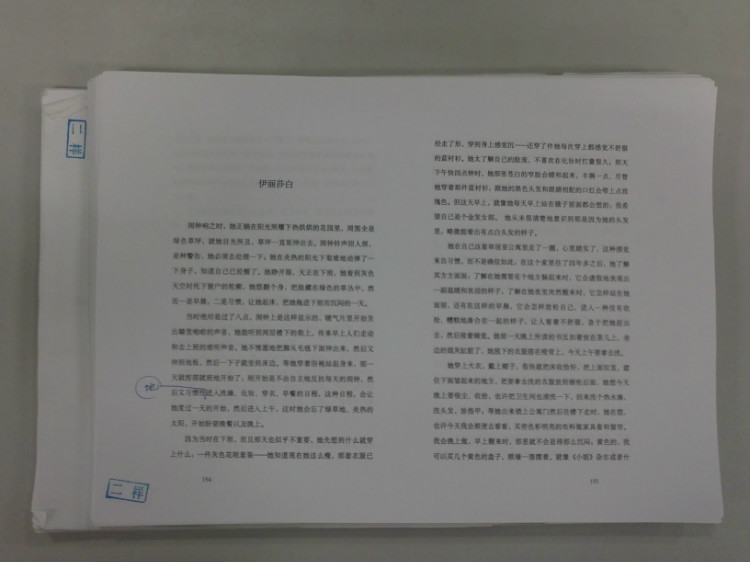I Shoot
 在广州也喝到了卖的胡辣汤,比我用汤料做的强,味道也正宗。3元一碗,旁边是从另外一家河南小饭馆里买的烧饼,1元一个,在一起就是的道的河南早餐。天河区的棠下有不少河南人,多数是来自驻马店、周口的的士司机及家属,所以这里颇有几家河南小馆。 科韵路“山东老家”的“擀面鲈鱼”。 "全家"超市的咖哩鸡饭。
我妈给我做了芝麻叶面条,河南老家的味道。老家人们把芝麻叶焯熟晒干,吃时泡开或凉拌、或下面条,略有苦味,永远难忘。
棠下的“阿强酸菜鱼”食客如云,光是门口等位的就有这么多,还不说门右侧还有几堆人。有几群有备而来,打起了扑克。
在广州也喝到了卖的胡辣汤,比我用汤料做的强,味道也正宗。3元一碗,旁边是从另外一家河南小饭馆里买的烧饼,1元一个,在一起就是的道的河南早餐。天河区的棠下有不少河南人,多数是来自驻马店、周口的的士司机及家属,所以这里颇有几家河南小馆。 科韵路“山东老家”的“擀面鲈鱼”。 "全家"超市的咖哩鸡饭。
我妈给我做了芝麻叶面条,河南老家的味道。老家人们把芝麻叶焯熟晒干,吃时泡开或凉拌、或下面条,略有苦味,永远难忘。
棠下的“阿强酸菜鱼”食客如云,光是门口等位的就有这么多,还不说门右侧还有几堆人。有几群有备而来,打起了扑克。